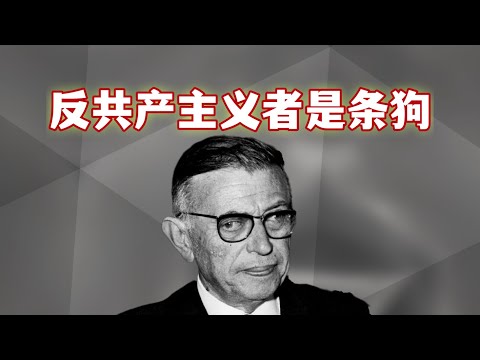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現實
知識分子通常是激進的。他們渴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卻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他們愛人類,卻不愛具體的人。
盧梭的理想與現實
盧梭在其著作《愛彌兒》中試圖告訴人們如何教育出理想的公民。然而現實是,他拋棄了自己的五個孩子,將他們全部送進了孤兒院。儘管他有自己的理由,比如擔心無法照顧孩子。
伏爾泰與盧梭的恩怨
另一位偉大的知識分子伏爾泰一直對盧梭頗有微詞。他曾在給盧梭的信中寫道:“從沒有人用這麼多智慧讓我們變得愚蠢。讀你的傑作讓人想趴在地上用四條腿走路。”後來,伏爾泰還寫了一本小冊子《公民的情感》,揭露盧梭混亂的私生活和拋棄嬰兒的冷酷行為。為了避免繼續被責罵,盧梭寫下了聞名世界的《懺悔錄》。
薩特的愛人類觀
今天的男主角之一薩特也是愛人類的典型。他的代表作《髒手》中有一句經典台詞:“我愛人,但我愛的不是他們現在的樣子,而是他們應該成為的樣子。”知識分子不僅想改造世界,還熱衷於改造人類。想到要變成他們喜歡的樣子,就讓人不寒而慄。
薩特在中國的名氣可能與他的親共立場有關。有人說薩特像魯迅一樣,是反傳統的紅色偶像。
薩特的成長與經歷
1905 年,薩特出生在巴黎,父親早逝,由外祖父撫養長大。外祖父是一位語言學教授,家中的知識分子氛圍讓薩特受益匪淺。孩童時期的薩特就厭惡和排斥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這為他日後成為親共人士奠定了基礎。
1924 年,薩特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學習哲學。1929 年,他遇到了同樣親共的作家波伏娃。兩人簽訂了一份“契約”,成為終生的精神伴侶——在維持彼此感情的同時,也允許對方有其他的愛情和性關係,並且及時分享各自的浪漫經歷。
波伏娃的情感經歷
很多年輕女性可能都喜歡波伏娃,她作品中的敏感和浪漫只有女性才能理解。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她逐漸發現了那些浪漫背後的殘酷和醜陋。波伏娃曾將自己的一名女學生介紹給薩特,結果自己也愛上了她。波伏娃、薩特和這名女學生的未婚夫至少有五個共同的情人。這些混亂的男女關係傷害了很多年輕人,其中有女孩自殺。1943 年,一個名叫娜塔莉的女孩的母親向警方提出控告,指控波伏娃腐蝕未成年人,並擔任“皮條客”為薩特和自己的女兒牽線。波伏娃因此丟了工作,但沒有受到法律懲罰。當時有報紙這樣評價薩特:“我們都熟悉薩特先生,他是一個古怪的哲學老師,專門瞄準女學生的內衣。”
薩特的戰爭經歷與思想轉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薩特應徵入伍,很快被俘,在德國戰俘營度過了十個月,於 1941 年獲釋。1943 年,38 歲的薩特發表了《存在與虛無》。那句經典的“他人即地獄”來自他後來寫的劇本《間隔》。
雅爾塔會議後,世界秩序和格局重新形成並固化。法國知識界逐漸分裂成幾個不同的陣營,以薩特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成為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說:“蘇聯有特權,因為它的目標是——所有人的正義和自由。”“沒有任何可以想象的情況能讓我們放棄對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
1952 年,薩特發表《共產黨與和平》,認為工人階級不能對共產黨表示懷疑。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還說:反共產主義者就像狗一樣,我堅持這樣看,也將一直這樣看。
從此,薩特和共產黨對暴力歷史有了相同的看法,所以蘇聯發生的所有暴力事件在薩特眼裡都無足輕重——因為這些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加繆批評蘇聯盛行的集中營制度,薩特立即回應:“是的,我同意你的觀點,這些集中營是不可接受的,但資產階級報紙每天都在用集中營來宣傳同樣不可接受的東西。”薩特的激進言論使他在法國大受歡迎,而反蘇的加繆則孤立無援。“加繆拒絕加入時髦的激進群眾……所以他受到薩特派的嘲笑和侮辱。那時,幾乎所有人都是薩特派。”
薩特與共產黨的互動
同樣是在 1952 年,薩特出席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原本計劃在大會期間演出薩特的著名劇本《髒手》,但薩特知道共產黨不喜歡這部劇。他決定在共產黨還沒提出要求之前就停止演出,並支付了相關費用。他公開表示,未來任何這部劇的演出都必須得到共產黨的批准。
1953 年,薩特發表文章憤怒譴責美國以間諜罪處決羅森堡夫婦,認為美國“明天就可能把我們所有人都拖入一場滅絕戰爭”。但就在薩特發表文章的那天,東德政府向和平抗議的工人開火,薩特卻保持沉默。左翼媒體試圖淡化“柏林屠殺”。
1954 年,薩特訪問蘇聯,受到隆重接待。薩特看到了一個在“秘密警察”領導下充滿希望的國家。回到法國後,他為蘇聯唱讚歌,聲稱:“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蘇聯人民不是無能的。他們可以自由出國,但他們不願離開自己美麗的國家。”
薩特與波伏娃訪華
1955 年,薩特和波伏娃來到中國,受到中共的高規格接待。他們在國慶節登上天安門城樓,與茅盾夫婦同桌觀看煙花。薩特和波伏娃高度讚揚中國的農村集體化,告訴歐洲人共產主義在歐洲和中國一樣適用。波伏娃後來在回憶錄中表達了對毛主席的喜愛:“毛澤東與中國領導人平靜地走在一起,最迷人的是他們沒有矯揉造作。”她評價中國人:“在這些臉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們的眼睛裡你看不到畏縮的目光,你看到的是情感。”
理想的破滅
但事情很快發生了變化。1956 年,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其殘酷程度震驚了天真的歐洲知識分子。不久,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殘酷鎮壓要求自由的人民。不久之後,中國開始了大躍進,幾年後發生了大饑荒。1957 年的饑荒和中蘇共產主義神話的破滅使薩特公開反蘇。他譴責蘇聯入侵匈牙利,並宣布與那些支持入侵的人斷絕關係。
然而,他的革命思想和進步事業並沒有停止。1960 年,薩特和波伏娃訪問古巴,稱讚古巴是“直接民主”,並感慨“這是革命的蜜月期”。同年,兩人來到巴西批評戴高樂,受到當地的熱烈歡迎。
1968 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蘇聯出現“布拉格之春”。被激情燃燒的天真法國年輕人開始把毛澤東當作他們的新偶像。法國大學生為反對越南戰爭而暴動,像紅衛兵一樣舉著毛澤東的肖像,高喊“打倒資本主義”!此時,儘管薩特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但他越來越提倡暴力。他和波伏娃發表聲明支持學生運動,還在大學發表演講,“暴力是學生手中唯一剩下的武器。”
薩特的後期活動
五月風暴後,薩特成為左翼報紙《解放報》的主編。1973 年,薩特幾乎失明。1974 年,他拖著病體前往西德與被拘留的紅軍旅成員對話。紅軍旅是德國的一個左翼組織,自認為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搶劫銀行,實施恐怖襲擊,在過去 30 年裡造成 34 人死亡,無數人受傷。
1980 年,薩特去世。劉曉波先生在他與加繆的文章中介紹了薩特,引用了法國知識分子列維對薩特的評價。列維說:“這位知識分子的歷史也是 20 世紀的歷史。知識分子的錯誤在於他們執迷於將布爾什維克革命視為新的曙光。我認為這種對純潔的瘋狂追求是 20 世紀的大問題。”事實上,這些話今天仍然適用於那些充滿激情的年輕革命將軍們。
令人驚訝的不僅僅是他們對暴力的熱愛,還因為他們可以用高超的口才和寫作來為自己辯護。
其他知識分子的經歷
著名的英國劇作家蕭伯納在 1925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晚年,他成為一名崇拜蘇聯的社會主義者。1931 年經濟危機期間,資本主義世界陷入困境。75 歲的蕭伯納訪問蘇聯,受到斯大林的接見和全蘇聯的熱烈歡迎。蘇聯媒體稱讚他為“歐洲最勇敢的思想家”。蕭伯納投桃報李,深情地說:“我環顧四周,看到每個人臉上都有一種新的表情,這種表情在資本主義的西方是看不到的。”訪問結束後,蕭伯納回到歐洲,告訴媒體所謂的饑荒謠言都是謠言。他可以證明蘇聯的食物供應隨時都很好,他對記者說:“回到資本主義是地獄。當你親眼看到布爾什維克時,你就不會有任何懷疑,資本主義註定要滅亡。我離開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回到了一個充滿絕望的國家。”一些記者忍不住問:“你為什麼不留在蘇聯?”蕭伯納機智地回答:“英國確實是地獄,但去地獄是我的責任。”蕭伯納是一類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有著獨特的天真,認為收入不平等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他提倡平等分配——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困是被禁止的。”然而,從他不想住在偉大的蘇聯而選擇住在像地獄一樣的英國這一事實來看,他也有著知識分子特有的“言行不一”。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很早就加入了瑞士的法國共產黨,並與流亡的列寧和季諾維耶夫有過接觸。1932 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會上,羅曼·羅蘭說蘇聯是各國人民的榜樣和希望。然而,訪問蘇聯後,羅曼·羅蘭也看到了許多問題。在他的日記中,他諷刺斯大林搞個人崇拜——花六個小時欣賞自己的神化儀式。他認為蘇聯是一個失控的專制制度,但為了保護蘇聯,不給反蘇勢力提供借口,羅曼·羅蘭要求他的日記必須在 50 年後出版。
除了薩特、蕭伯納和羅曼·羅蘭等親蘇派,還有一些歐美知識分子親自投身於革命洪流。新西蘭知識分子艾黎自 1927 年首次來到中國後,一直積極參與中國的慈善和民主事業,並於 1935 年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艾黎有著知識分子為理想獻身的偉大精神。在陝西時,他住在條件極其艱苦的窯洞裡,先後創辦了機械、造紙、紡織、製革等 17 個工業合作社,還在嘉陵江上安裝了水輪發電機,讓雙石鋪第一次用上了電燈。1949 年,艾黎選擇留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感到震驚。他被監禁,目睹了周圍的一切。在宋慶齡介入救了他的命後,艾黎於 1987 年在北京去世,享年 90 歲。
與宣傳思想的外圍知識分子相比,現代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史沫特萊的介入顯然更深。美國陸軍將軍威洛比曾聲稱她是理查德·佐爾格手下的間諜。史沫特萊為此想起訴他。一些美國媒體也說她可能是“三重間諜”——為中國共產黨、印度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工作,是 20 世紀最多產的女間諜之一。
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
從各個知識分子的經歷不難看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想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而且大多數人提倡暴力。事實上,他們用暴力來實現偉大目標的做法至今是否應該,仍然是人們熱衷討論的話題。
薩特的劇作《間隔》
在節目的最後,讓我們拋開這些意識形態,單純地談談藝術。儘管薩特支持共產主義,私生活混亂,但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劇作家。他的《間隔》講述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三個死人陸續來到地獄,卻發現這裡既沒有刀山火海,也沒有刑具,只有一個小客廳。這三個人分別是被槍決的報紙編輯加爾森;死於煤氣中毒的郵政員工伊內斯;死於肺炎的貴婦人埃斯特爾。
當這三個人在地獄相遇時,他們彼此警惕,隱瞞自己生前的惡行:加爾森竭力讓別人相信他是英雄,事實上他是二戰中因臨陣脫逃而被處決的懦夫,還是一個沉迷於酒精和性、折磨妻子的虐待狂;埃斯特爾隱瞞自己的蕩婦身份和殺嬰罪行,裝作是為了年老的丈夫犧牲青春的貞潔女子;伊內斯則竭力掩飾自己的同性戀過去。
這三個人不僅彼此封閉,還互相折磨。他們每個人都時刻存在於“他人的目光”中,受到審視和監督。由於他們生前的惡習沒有改變,他們的真面目很快就暴露了。一旦暴露,他們就毫無顧忌,形成了一種相互追逐、相互排斥的雙向三角關係。這三個痛苦的靈魂就像坐在旋轉木馬上,進入了一種誰也得不到、誰也不能安寧、誰也無法退出的地獄。最後,加爾森意識到:“何必用烤架,他人就是地獄!”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我是溫婷,我們下期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