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活在未来的现象
-
社交媒体上有关“00 后养生能存多少钱”“00 后不生孩子谁来照顾健康”“00 后开始担忧健康问题”等话题引发关注。这让人想起今年三月的热门话题“被退休恐惧支配的中国人生活”。中国人似乎一生都在为未来做准备,从婚姻、生育到工作,都围绕着“养老”。
-
成长过程中,我们常听到各种“等……就……”的话。学生时代,老师和家长说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才能过上好日子;大学毕业,家人和教授说找到工作就自由了;工作后,领导说做完项目就能升职;有了积蓄,父母和朋友说要赶紧买房;结婚、生子、孩子长大、退休、疾病治愈,仿佛每个阶段都是为了下一个阶段,中国人成了活在未来的人,有一套固定的人生公式,前半生为后半生准备,后半生为死亡准备。
中国人高度未来导向的原因
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导致的不安全感
-
具体表现之一是极高的储蓄率。中国人有强烈的存钱习惯,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 1980 年到 2023 年,中国居民负债率长期保持在 36% - 45%,而同期发达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居民负债率基本在 15% - 20%波动。中国 GDP 占世界不到五分之一,却贡献了世界总债务的四分之一。2024 年,美国债务仅为中国的 40%,消费却是中国的 2.69 倍。疯狂存钱不花钱,表明中国家庭普遍选择牺牲当前消费享受,为未来存钱抵御风险。
-
背后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不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时,人们只能用更多的家庭和个人储蓄来应对风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钱才能在遇到疾病、失业等意外时生存。若存钱是人们应对未来风险的唯一底线,那制度必然存在问题,是制度造成了全社会的未来导向,让人们焦虑。
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压力
-
教育竞争激烈且成本高,父母会为了下一代的未来牺牲当下享受,这直接增加了家庭储蓄需求。
-
住房方面,有房才有家,未来才不会流落街头。即便房价上涨、房地产市场变化、出生率下降,年轻人仍会努力付首付,成为房奴,几十年还债。各种社会现实使中国人形成了集体的延迟满足感,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但在制度压力下,活在未来成了看似理性的选择。
伦理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影响
-
中国文化一直强调过去已逝,未来可期,有宗教般的追求未来的统一感。著名跨文化研究者霍夫斯泰德提出了与短期导向相对的长期导向文化维度,中国在这一维度得分很高,注重未来回报,强调体面和毅力。成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都体现了这种观念。传统家庭观念中,“养儿防老”是首要,养儿是抵御未来不确定性的最佳投资。
-
另一方面,中国家庭受时间高度束缚。父母深度参与孩子的生活,在学校、婚姻、职业选择上有强烈干预。干涉孩子婚姻的本质是担心孩子未来,怕孩子孤独无依,也包含传宗接代的传统愿望。他们认为孩子只有走正确的路才能避免未来的问题,个人被家庭角色定义,孩子要承担未来照顾父母的责任,父母要为孩子铺路。
老龄化社会和养老金制度危机
- 老龄化社会使年轻人处于“未富先老”“少子化”状态,要照顾父母又不想生孩子,担心自己老无所依。同时,国家养老金制度面临危机,若 2035 年养老金耗尽,90 后、00 后将没有养老金,很多人甚至不缴纳社保。这意味着传统家庭和国家养老模式不再有保障,年轻人过早担忧养老问题。
儒家文化对“吃苦”的强调
- 儒家文化强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观念在农业文明时代有现实合理性。年轻时多吃苦,年老时才不会受穷,成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很多历史故事也强化了这种信念,认为通过吃苦能走向成功和幸福。尽管现代年轻人开始反思“吃苦文化”,但他们的反思多体现在与上一代生活方式的冲突上,从小接受的价值观仍是“吃苦”。
中国教育的影响
- 中国教育从小就培养孩子活在未来。暑假要上辅导班学习下一年的知识,孩子出生后的假期常是学前准备期,有些父母甚至让孩子提前学习下一阶段的知识。整个教育过程中,学习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高考、未来工作,这大大降低了学习的乐趣。“远大抱负”“光明未来”在中国教育中被高度赞扬。
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心理差异
-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时间的悖论》一书中,将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类型,每种倾向又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
活在过去分为消极过去和积极过去。消极过去型会专注于过去的不快乐和遗憾,反复纠结过去的错误和伤害;积极过去型喜欢回忆美好的旧时光,从过去的经历中获得安慰和认可。活在过去的优点是与根源、家庭和身份有联系,缺点是过于消极易陷入后悔和停滞。
-
活在现在分为享乐主义现在和宿命主义现在。享乐主义现在型追求当下的快乐和刺激,及时行乐,把握眼前,热爱社交冒险和新体验,充满活力但可能缺乏长期规划和忽视风险;宿命主义现在型觉得生活不由自己掌控,对未来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可能缺乏规划和行动积极性。
-
活在未来分为目标导向型和超越死亡型。目标导向型通常会延迟满足,为了未来牺牲当下,如努力存钱、制定长期人生计划,相信当前的付出会带来长期回报,但过度的未来导向会牺牲当下体验,导致后期压力和空虚。
如何寻找时间观的平衡
活在当下
- 埃克哈特·托勒在《当下的力量》中提出,若不能在当下找到平静,就永远找不到,因为除了当下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中国人总觉得在某个时间点生活能开启新篇章,其实那个时间永远不会来。当我们活在当下,会发现过去和未来只存在于思想中,是意识的延伸。活在当下不是不规划未来,而是规划后在当下全力以赴,不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困扰。比如想成为作家,不要等有空闲时间,现在就拿起笔开始写。
重建附近
-
人文学者项飙提出“附近的消失”概念。工业化后,抽象的时间和时钟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不再通过空间衡量,空间逻辑消失,这被称为“去空间”或“时间的暴政”。附近是空间,附近空间的消失是因为时间的暴政,也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依赖抽象概念和原则,而非对周边空间的感知。
-
项飙建议重建附近,附近有很强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包含许多看似不重要实则重要的社会关系。年轻人一方面关注自己的考试、毕业去向、工作和薪资,另一方面受社交媒体上宏大叙事的影响,情绪波动大,对周围生活感知模糊。重建附近,就是在巨变和不确定的时代,从身边可触及的生活空间中寻找锚点,与当下具体环境中的人事物建立连接,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比如了解邻居的职业、楼下打扫卫生的人的来历、他们的焦虑和梦想等。重建附近是平衡时间的可行方法,鼓励年轻人走出时间的暴政和未来的焦虑。
总之,中国人活在未来是由体制、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活在未来并非解决之道,应将未来时间导向适当平衡到当下,通过活在当下和重建附近,找到时间观的平衡,更好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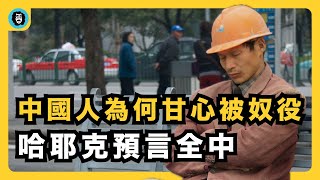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