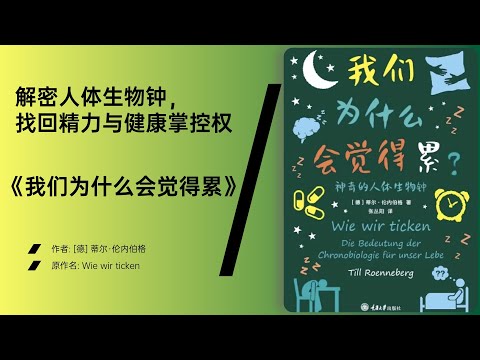疲勞背後的深層邏輯
大家好,歡迎來到每日一書。今天要講的是一本貼近每個人身體感受的科學書,名字叫《我們為什麼會覺得累》,作者是德國著名的生物節律學家蒂爾·倫內伯格。
許多人一聽到書名,可能會認為疲勞就是因為工作多、休息少、睡不好。然而,這本書揭示疲勞背後的邏輯遠非“缺覺”那麼簡單。我們感受到的疲憊,是一種深層次的“時間錯位”問題。
現代社會讓我們處於“持續性社會時差”狀態。身體想休息時被鬧鐘叫醒,大腦最活躍時被迫發呆,真正休息時間卻用來刷手機、加班、應酬。生理節律被打斷,越來越多人整天覺得累,甚至習慣到察覺不到。
睡眠的“時間質量”
很多人明明睡了七、八個小時,醒來卻依然頭重腳輕、心煩意亂。大量調查發現,很多人不是睡眠時間不夠,而是睡眠時機錯了。睡眠的“時間質量”比“時長”更重要。
我們的身體就像一支交響樂團,每個器官是樂手,大腦深處的生物鐘是指揮家。若指揮家失靈,樂手各吹各調,就變成噪音,即我們感受到的疲憊、混亂、焦慮等。
但現在,生物鐘這位指揮家根本沒機會工作。鬧鐘剝奪其對清晨節律的掌控,咖啡因干擾白天節奏,手機屏幕藍光打亂夜間信號傳遞。
社會時差:現代人疲憊根源
倫內伯格提出,我們每天的時間安排與生理節奏出現類似“時區錯亂”的狀態,他稱之為“社會時差”(social jetlag)。身體的生物時鐘在一個時區,人類生活節奏卻強行調在另一個時區,這種內外時間不一致,才是現代人疲憊的真正根源。
傳統觀念把疲勞歸因於工作多、作息不規律或精神壓力大,卻忽略人類天生不是在標準時間表上運作的生物。有些人是“早起型”,有些人是“夜貓子型”,但社會幾乎為“早起型”人設計。
學校早上七點半上課,許多青少年在成長期自然向“晚型節律”偏移,卻處於長期睡眠剝奪狀態。上班族在工作日也處於“反節律”生活狀態,長年累月導致“慢性疲勞狀態”,睡足也無法真正恢復。
被社會麻痹的疲勞感受
我們對疲勞的感受正被社會麻痹,越來越把“累”當成常態,甚至把“熬夜”“疲憊”“加班”當成炫耀的奮鬥姿態。但身體會通過注意力下降、短期記憶紊亂、情緒易怒、胃口紊亂、免疫系統出錯等方式發出抗議,我們卻常誤以為是“壓力大”或“老了”的正常現象。
很多人放假後第二、三天才真正進入放鬆狀態,真正恢復活力要到假期第五天甚至第七天,但大多數假期只有三天或五天,很多人一輩子都沒真正休息過。
理解自己的身體時區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能拋棄鬧鐘、拒絕社會節奏、任由作息混亂。倫內伯格真正想說的是:你必須理解自己的身體時區,然後盡可能讓生活靠近它。只有“社會時鐘”向“生物時鐘”靠攏,我們才能真正感受到輕鬆和清醒。
疲勞不是懶惰的結果,而是時間錯位的信號。若總覺得累,也許不是不夠堅強,而是時間線和身體節奏不在同一頻道上。
操控體內節奏的力量:生物鐘
理解疲勞感可能來自“時間錯位”後,接下來要了解操控體內節奏的力量。蒂爾·倫內伯格用幾章內容解釋了關鍵機制——生物鐘,更準確地說是“晝夜節律”。
我們體內每個細胞都有自己的節奏,與晝夜變化高度協同。這個節律最核心的調度中心是大腦下丘腦的“視交叉上核”,它接收光照信號,安排各種生理功能的時間。
但現代社會正在系統性地擾亂這套機制。人類文明出現前,對時間的感知來自太陽;現在,節奏主要被人造光源、鬧鐘、工作時間表左右。尤其是藍光屏幕,在夜間釋放的藍光足以延遲褪黑素分泌,形成“睡眠拖延型疲勞”。
社會時差的真實影響
“社會時差”是真實可測的生理現象。以晚型人為例,自然狀態下凌晨一點入睡、早上九點醒來,若要早上七點打卡上班,每天就被剝奪兩小時自然睡眠窗口,工作日處於“功能性清醒”,周末補覺又被視作“懶散”,大腦和身體在節奏衝突中積累失調。
調查發現,社會時差最大的群體,即自然生物鐘與現實作息最不匹配的人,更容易出現慢性疲勞、焦慮、抑鬱、暴飲暴食、甚至代謝類疾病,主觀情緒和客觀生理數據都呈現異常。
被誤解的“早起”
人群中“早起型”和“晚起型”的差異可達五個小時,這是人類天然的生物鐘分佈特性。但我們太信任“鬧鐘”,鬧鐘是人類發明史上最具破壞力的技術之一,把“外部時間”強行蓋在“生物時間”之上。
我們還經常拿“早起”當作衡量自律的標準,但其實“早起型”只是社會機制偏愛他們的節律類型,把“早起”看成美德只是因為它更方便社會時間表運行,而非更健康、更科學。
被邊緣化的晚型人
“MSF”(mid-sleep on free days),即“自由日中點睡眠時間”,可以精確測量一個人的生物鐘類型。現代社會中晚型人占比超過三分之一,卻是最被制度邊緣化的一群。
從上學開始,晚型孩子就被貼上“不專心”“拖延”“愛犯困”的標籤;長大後,成為“打工人”里最常遲到、最難約早會、最常被誤解的人。這不是他們懶惰,而是社會沒給他們與節律匹配的空間。
對疲勞和睡眠的誤解
蒂爾·倫內伯格揭示了一個事實:我們不僅誤解了“疲勞”,更誤解了“睡眠”本身。從上學開始,我們被教育要“早睡早起”,但每個人的生理節奏可能完全不同,“標準作息”不適合所有人。
“睡八小時就夠了”這種說法忽略了“什麼時候睡”和“是否自然醒”兩個關鍵變量。睡眠也不是“體力恢復”的主要環節,而是“腦部重組”的過程。
一個人是“早起型”還是“夜貓子型”,是由基因決定的。同卵雙胞胎即便在不同環境下長大,睡眠節律依然高度相似。如果節律是生理基礎,那社會對“晚型人”的壓制,其實是一種結構性歧視。
節律錯位引發的健康問題
節律錯位不僅讓人累,還會引發廣泛的健康問題。長時間處於節律不匹配狀態下的人,更容易患上糖尿病、肥胖、抑鬱、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
很多人注重健康,吃得清淡、運動規律、每晚保證七小時睡眠,卻依然覺得累,就是因為身體始終沒有“活在自己應在的時間里”。疲勞不是行為問題,而是時間結構的問題。
找回適合自己的節律
研究人員在無時鐘、無窗戶的環境中,讓志願者自由安排作息,結果大多數人不會自動進入“標準作息”,而是出現高度個體化的節律。
倫內伯格說,我們所謂的“自律”,有時候不過是馴服,真正的自由是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律。只有認清自己的節律類型,據此調整生活方式、安排重要任務、選擇工作時間,才能從根本上緩解“無休止的累”。
生活中的自我觀察與調整
在生活中,人們可以做一些自我觀察:什麼時候自然醒來、注意力最集中、入睡最不難受。這些信息是身體的提示信號。
他還提出“節律認知”,每個人都應像管理財務一樣管理自己的時間節奏,深度理解自己的時間結構,找出適合社交、工作、清空大腦的時間。
未來的健康不是靠吃藥、健身、早起打卡,而是靠人和自己的節律達成和解。
重新設計更貼合自然節奏的社會
走到書的尾聲,蒂爾·倫內伯格提出:我們有沒有可能重新設計一個更貼合人類自然節奏的社會?
他說,我們不是在呼籲人類“睡懶覺”,而是為每個人爭取“按照自己生物時鐘生活的權利”。
現在已有一些國家或地區在嘗試打破一刀切的作息制度。例如,芬蘭和丹麥的一些學校根據學生生理節律類型調整上課時間;荷蘭某些公司允許員工選擇“自定上下班時間”;德國有研究機構為僱員提供“節律測試”。
這些小範圍實驗不是對傳統的挑戰,而是對現實的正視。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的時間感是彈性的,是大規模工廠和學校制度把人拉入“統一時間秩序”的軌道。數字時代的到來,讓我們重新具備“節律自由”的技術條件。
個體的節律意識覺醒
但單靠制度不夠,個體的“節律意識覺醒”才是第一步。他提倡“時間自決權”,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一天中的關鍵行為節點。
如果你不確定自己的生物節律類型,可以從“記錄一周的自然作息”開始,不用鬧鐘、不刻意改變,記錄入睡和醒來時間、腦子最清楚的時間等,找出自己的“節律地圖”。
然後進行“結構微調”,在原有結構中做出微小改變,如把重要會議安排在最清醒時段、運動挪到身體最容易接受的時間段等。
不要用社會評價定義健康
不要用“社會評價”來定義是否健康。社會推崇“早起的人”“白天高效的人”“夜晚安靜的人”,但這套標準沒考慮個體差異。
如果晚上十一點才開始思維活躍,不要因不合群而自責;如果需要午睡,不要因別人不睡就感到羞恥。節律不是德性,而是生理,我們不需要道德化自己的疲勞。
關注孩子的節律
永遠不要忽略孩子的節律。很多父母焦慮孩子成績不好、情緒波動,卻每天清晨強行把他們叫醒上早課。青春期是“晚型化”最明顯的階段,學校卻把他們拉進“晨型懲罰制度”,這是對生理發展規律的直接背離。
倫內伯格希望未來教育制度能提供“節律分班”的選項,讓孩子在更適合的時間里成長。他甚至設想一個城市根據不同節律類型分區運行,人們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至少別誤解自己
在真正的大制度下,每個人都有身不由己的部分。當每天早上睜開眼感到疲憊,不要急著怪罪自己不努力,不要用“拖延”“懶惰”壓自己,試著問問自己:時間結構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設錯了時區?
整本《我們為什麼會覺得累》不是教你如何“睡得更好”,而是教你如何“更清醒地理解自己的時間”。累,不只是身體的警報,也是節律的抗議。
好了,這本《我們為什麼會覺得累》就分享到這裡,歡迎在評論區分享感受,或者告訴我們你想聽的下一本書。讓我們一起,在書頁間旅行,尋找更多的感動和啟發。謝謝收聽,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