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其人與其成名之路
哲學與 SuperY,讓你感受非凡!每一集都會為你介紹一位哲學思想家。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是盧梭的生日,恰巧連經出版為其經典著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出版五十周年重新印刷。
盧梭於 1712 年出生在現今瑞士的日內瓦,是瑞士哲學家。他在阿爾卑斯山區長大,熱愛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典。與其他哲學家不同,他未受過正規哲學教育,全靠自學,堪稱哲學神童。
15 歲時,盧梭成為一名雕刻師的學徒。一天因回家太晚城門關閉,怕被師傅懲罰,他索性流浪到其他地方。幾天後,他遇到沃倫夫人,被收養並送去教堂接受正規教育,改信天主教。但 16 歲時,他在教堂遭受性騷擾,投訴卻被視為胡言亂語。
後來盧梭前往巴黎找沃倫夫人,兩人相戀同居。他憑音樂才華在巴黎當音樂教師,靠譜曲賺錢。當時沒有大學哲學系,許多哲學家靠當私人教師謀生。
盧梭因音樂才華進入巴黎上流社會,認識了當時哲學界的核心人物狄德羅。狄德羅邀請他為百科全書撰寫音樂條目。狄德羅因發表“不存在先天觀念”的言論入獄,因為天主教會認為人有原罪,上帝是先天存在的,挑戰這些就是挑戰教會權威。
盧梭探監時看到報紙上的寫作比賽徵文,主題是“科學與藝術的復興對道德的淨化或腐敗有何貢獻?”他由此獲得靈感,寫了一篇文章,認為科學藝術越進步,人類文明越墮落,最終獲得第一名,名揚法國。
後來他再次參加寫作比賽,主題是“論不平等的起源”,這次的文章讓他從音樂家轉變為哲學家,這本書也成為歐洲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啟發了許多法國革命者,讓他們意識到不平等不是命運,社會可以改變。
盧梭對不平等起源的探索
要找到不平等的起源,首先要問:不平等是自然的,還是人類社會自身創造的?比如今天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很多人說這是人性,資本家只是展現了人性的貪婪,社會不平等只是自然不平等的衍生。這種辯護預設了不平等是自然人性,而不是社會塑造的人性,這樣一來,無論如何改變社會都沒用。但如果貪婪實際上是社會塑造的,卻被描述為天生的,那就是犯了謬誤。
盧梭認為,必須區分未被文明污染的人性和被文明社會社會化的人性,才能知道不平等何時開始出現。亞里士多德認為不平等在出生時就注定了,每個人天生智商、外貌、體能都不同,有些人就是天生幸運,基因好,所以在社會上容易成功,他以此為希臘人奴役外國人辯護,說希臘人天生更適合當主人。
盧梭要駁斥“不平等是由自然造成的”這一論點。假設有人天生有身體或精神殘疾,這被稱為先天不平等。但盧梭認為,先天盲人如何被對待完全取決於社會。在許多古代文化中,盲人被視為有預知能力,被尊為先知;但在重視勞動的工業社會,盲人被視為無用。所以不平等不是由自然造成的,而是人類自己造成的,自然本身沒有正義或不義的問題。
要知道不平等的起源,盧梭說必須設想一個未被文明污染的世界,他稱之為“自然狀態”。自然狀態意味著沒有任何人文因素干擾我們對人性的觀察,把人從社會中抽離出來,人可以像野生動物一樣自給自足,就像迪士尼的泰山。這種狀態能反映人性的原始面貌,相反,文明社會中的人已經被污染了。
盧梭讓我們比較自然界的動物和被人類馴化的動物。野狗更強壯,可以自己獵食,但馴化的狗失去了自己找食物的能力。盧梭說,人類本身就是被文明馴化的動物,文明使人類變得虛弱多病。自然狀態下的人其實更強壯,因為原始人靠體力狩獵,但文明發明各種工具後,人類自給自足的能力反而削弱了。如果把一個文明人扔進叢林,可能活不過一周。雖然文明擁有最先進的醫療技術,但在最先進的國家,公民卻遭受各種文明病的折磨,如抑鬱症、癌症、失眠,在盧梭看來,這是文明的症狀,是文明人自己創造的疾病,原始人根本沒有。
然而,儘管盧梭批評文明,他並不反對文明。他不是要大家回到原始部落生活,而是用它來打破現代人的幻想,即認為人性本惡,不平等源於某些人的自然性情。盧梭的觀點恰恰相反,他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下是善良的,不存在不平等問題,這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想法。
18 世紀的歐洲仍由教會統治,人們相信人有原罪,需要依靠教育和加入教會才能得救。盧梭卻提出人天生善良,進入文明社會後才墮落,這一理論在當時引起了巨大震動,他的幾本書也被查禁。
原始人性的構成
那最原始的人性是什麼樣的呢?盧梭認為最原始的人性由兩種力量組成。首先,人有自我保存的愛,這是人類最原始的動物性,人類的行為都是為了自我保存,讓自己活下去,這也是人們愛父母的原因,因為父母的照顧有助於生存,這種自我保存的本能不會導致壞的後果。一個原始人出去打獵是為了填飽肚子,不會造成不平等的社會。
你可能會反駁說,如果幾個獵人在競爭有限的資源,難道不會出現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從而導致不平等嗎?盧梭認為,這種想法是把現代人的觀點投射到原始人身上。在真正的原始生活中,根本不需要競爭資源,因為大自然到處都是水果和獵物,原始人根本不需要競爭,餓了就去山林摘水果。認為資源有限,需要長遠規劃,是只有文明人才有的心態,因為文明人住在城市,資源被富人控制,所以覺得資源非常稀缺,不了解大自然的豐富。盧梭甚至認為,“未來”的概念只存在於文明社會,原始人根本不需要擔心未來,只活在當下,努力生存。總之,利己的自愛不會導致不平等。
除了自愛,還有另一種有利於整個物種延續的人類特質,那就是同情心。人看到有情眾生受苦時自己也會感到痛苦,比如劇院觀眾看到野獸搶走孩子會感到憐憫,這種同情心在動物界也能觀察到,動物看到同類受苦也會感到同情。盧梭認為,這種同情心是幾乎所有美德和善行的源泉,所以同情心也不可能是不平等的起源。
除了自愛和同情心,還有兩種人類特質是動物沒有的:一是可完善性。一個人的內在潛力可以通過環境得到完善,比如語言能力,人天生有學習語言的潛力,但仍需要通過後天培養才能發展出來,而動物沒有學習語言的潛力,所以無論怎麼教都學不會。人類有無限的可塑性,可以被環境塑造,改變到甚至看不到原始本性的程度,這就是為什麼在盧梭看來,許多人性理論是錯誤的,它們根本不是在談論最原始的人性,而是被環境改變的人性。
最後,人類和動物的區別在於:人類有自由選擇的意志。動物只能遵循因果的自然規律,而人類可以抵抗。比如,餓是一種自然刺激,動物餓了就會找食物,但人類可以行使自由來抵抗餓,比如絕食。
在自然狀態下的這四種人類特質,自愛、同情心、可完善性和自由意志,我們在其中任何一種都找不到不平等的起源。所以盧梭認為,不平等一定不是起源於自然,自然狀態反而是人類生活最幸福、最健康的黃金時代,進入文明社會後才開始出現各種痛苦。
如果自然狀態這麼好,文明這麼苦,人類肯定不會自願離開自然狀態,一定是某個意外導致人類走向文明。所以雖然盧梭被歸類為左派,但他與大多數左派非常不同。左派一般認為啟蒙會給人類帶來歷史進步,但盧梭懷疑歷史是否真的在進步。與其說盧梭是啟蒙哲學家,不如說他是“反啟蒙”哲學家,他認為現代文明導致了人性的退化。
不平等的起源
盧梭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不平等不是起源於自然,它必然源於人類自己創造的東西。在論證了不平等的起源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類本性固有的之後,盧梭直接回答:那麼,不平等的起源是什麼呢?
盧梭認為,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從獨立、自給自足的原始人過渡到共同的人類社會,人們在休閒時間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人們會開始想:誰跳舞跳得更好?誰唱歌唱得更好?誰更有吸引力,更適合作伴侶?他們開始評價別人,比較誰更有吸引力。因為每個人都想成為心愛之人眼中最迷人的人。但一旦這種比較心理開始蔓延,人類的心理就開始惡化和腐敗。人們越來越關心別人的看法,渴望優越感,希望別人愛他們勝過愛自己。自然狀態下的“自愛”轉變為“虛榮”甚至“自戀”,這種心理就是盧梭所說的“amour-propre”(虛榮、驕傲)。
這種虛榮不是人性的原始狀態,而是社會塑造的扭曲狀態。因為自然狀態下的原始人不會比較誰擁有更多,就像松鼠積累堅果只是為了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讓其他松鼠嫉妒。原始人的優越感只施加在動物身上,比如發現自己跑得比獵物快,就覺得人類是優越的生物。但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人類的優越感實際上轉向了自己的同類。現在人們不僅要征服野獸,還要征服別人。每次遇到一個人,都會在心裡衡量他們,計算誰更有能力。即使你已經很富有了,只要遇到一個比你更富有的人,你仍然會覺得自己很窮,並渴望賺更多的錢。關鍵不是我實際擁有多少,也不是我是否真的需要更多,而是我在別人眼中是否顯得優越。
盧梭認為,這就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是因為人類的虛榮心,amour-propre,被喚醒了。從此,原始人變成了喜歡比較的生物,他們為別人的目光而活,追求比別人更好、更富有或更有吸引力。人類歷史上的各種邪惡都可以追溯到這種心理。
比如,財富不平等是如何產生的?盧梭認為,在人類文明中出現農業和勞動分工後,人們越來越依賴彼此的勞動,失去了自給自足的能力。原始人可以獨立生活,但文明人不能。有強烈虛榮心的人利用了這一弱點,圈佔了原本是公共財產的土地,告訴一群無知的人,這塊土地是我的私有財產,而這些人愚蠢地相信了。盧梭說:這就是文明的起源,是有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把私有財產的概念引入了社區,讓人們忘記了土地不屬於任何人。在法語中,虛榮(Amour-propre)和財產(propriété)有相同的詞源。
但佔有土地還不夠,因為那些被剝奪土地的人可以聯合起來反抗,所以富人必須聯合起來創造一個國家,讓國家建立軍隊來保護富人的財產,制定法律,定義什麼是正義。所以當窮人想反抗時,國家就會派軍隊鎮壓他們,並告訴窮人:你們是先擾亂社會秩序的人,你們是不公正的一方,這使得不平等看起來合法。
所以,在盧梭看來,財富不平等不是源於經濟問題,私有財產、國家、法律制度——這些都是為了維持不平等而衍生出來的,真正的根源其實是心理問題。當人們看到自己比別人擁有更多時,就會感到優越感。不平等不是因為人類的貪婪,古代的國王和今天的資本家,他們真正渴望的不是錢,而是用財富支配別人的快感,能夠讓別人嫉妒,覺得自己優越,這種支配感比錢本身更令人滿足。
在盧梭看來,那些擁有大量財富的人其實渴望別人的關注,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直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生活只是不斷積累財富,讓別人嫉妒。
除了財富不平等,盧梭認為愛情背後的心理機制也與 amour-propre 有關。因為當你愛上一個人時,就等於承認這個人對你最有吸引力,是你愛人眼中的第一名。人類發明婚姻是為了滿足人們的 amour-propre,和某人結婚就像向社會公開宣佈,你是我認為最好的人,你贏得了其他競爭對手。這也是為什麼盧梭認為人不應該出軌,因為這是親自破壞你曾經給予伴侶的認可,就像踐踏別人的自尊。
這也是文明人和原始人的區別,原始人不需要婚姻制度,也沒有愛情忠誠的概念,他們只是遵循原始的衝動,不斷尋找性伴侶,也不會因此感到嫉妒或羨慕。
我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很多行為其實都是由 amour-propre 驅動的。比如,很多人健身是為了自己的健康,還是為了獲得別人的羨慕目光?很多父母說教育是為了孩子好,但到底是為了孩子自己的發展,還是為了讓別人覺得他們善於教育孩子?盧梭的理論可以用來重新理解我們與自己和他人的關係,想想當我們做某件事時,是為了讓別人嫉妒我,獲得別人的認可,還是我真的是為了自己?
不平等的危害
在指出不平等的起源是 amour-propre 之後,盧梭進一步論證為什麼不平等是壞的。盧梭認為,不平等必須受到批評,因為它有不道德的後果。
首先,經濟不平等導致自由的喪失。人越窮,越容易被富人支配,因為窮人必須依靠資本家給他們工作才能吃飯,他們也被迫服從資本家的意志。那麼為什麼窮人不能拒絕工作呢?因為在高度專業化的現代社會,你的衣食住行都依賴於其他工人的勞動,為了獲得這些產品來滿足你的需求,你必須工作賺錢,犧牲你的自由為資本家工作。
換句話說,文明社會奴役公眾的方式實際上是通過人為的需求來創造依賴。因為你不能自給自足,你需要依靠市場上的商品,所以你必須犧牲你的自由來賺錢。你越依賴別人生產的商品,你就越需要賺錢,你犧牲的自由就越大,這導致了文明人奴性的性格。即使公司不強迫員工,員工也會不斷奉承上司和老板,因為這是取悅生活的方式。
相比之下,原始人不需要取悅任何人,因為在沒有專業分工的史前時代,原始人靠自己解決衣食住行,他們不依賴任何人,所以可以保持獨立和自主。比如,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灣的一個漁獵部落 Ichthyophagi 後,發現他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根本不在乎文明的東西,亞歷山大大帝不得不強迫他們放棄吃魚,切斷他們的生計,才能統治他們。
比如,我們經常說在台灣出去吃飯很方便,這給人一種自由的感覺,你可以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但盧梭會說,這是不自由的表現,因為你會過度依賴出去吃飯,失去自己做飯的能力。如果有一天所有的餐廳都關門了,你就只能等死。
在盧梭看來,要擺脫不自由的狀態,你必須判斷我的需求是真實的還是社會創造的虛假需求。真正的需求得到滿足後,你會感到更滿足和自由,虛假的需求得到滿足後,你會感到更不自由,更依賴社會。比如,社交媒體上的點贊數和流量,在盧梭看來都是虛假需求,其背後的邏輯是你想要別人的關注和讚美,這意味著你生活在別人觀點的統治下,你必須迎合大眾口味來創作內容,你越在意觀看次數,你就越依賴別人,最終失去的是你自己的自由。可怕的是,你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一旦虛假需求成為一種習慣,你就會覺得它們是真實的需求。
比如,很多富人消費,不是為了滿足真實需求,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進行炫耀性消費,購買奢侈品,到處旅遊,以突出自己比別人優越。這些人看似是在為自己消費,但實際上他們在消費時想的是別人,想著如何讓別人嫉妒和羨慕。
後來,二戰後,德國哲學家馬庫塞發展了一種與盧梭非常相似的虛假需求理論,用來批判當代高消費社會。他認為,許多需求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使人們更容易依賴市場,以便統治。事實上,早在 18 世紀資本主義剛剛萌芽的時候,盧梭就已經批評過這種現象,並更清楚地指出了其背後的心理機制。
除了自由的喪失,盧梭認為不平等還有另一個負面後果,那就是它損害了社會大多數人的福祉。盧梭說,即使社會最底層的人能夠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貧富差距過大仍然對人們有害。為什麼?因為人類的 amour-propre 渴望得到別人的平等尊重,被當作人來對待,但社會上的窮人卻被別人看不起。所以盧梭批評不平等,不僅僅是因為物質貧困,還因為心理因素。
讓我們想象一下,社會最底層的人拿到最低工資,雖然他們能負擔得起一日三餐,但他們仍然被視為公司的奴隸或失敗者。與此同時,他們每天看到社會上有很多億萬富翁過著令人羨慕的生活,這立即在底層人民心中產生了一種挫折感。
支持資本主義的人會說,這給了窮人更多的動力去賺錢,扭轉局面。這種論點根本不理解盧梭的批評,因為即使你今天賺了很多錢,上升到中產階級,有了房子和車子,只要 amour-propre 的心理機制仍然存在,你就會繼續和那些更高層的人比較,看到別人擁有更多,你就會感到渴望,你仍然會感到不滿足。
所以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里,所有階層的人實際上都變得更不幸福,因為每個人都想往上爬,但沒有盡頭。每當你爬上一個階層,獲得一點滿足感,一旦你看到上面的人擁有更多,你的滿足感就會立即消失。
那麼如果人們爬不上去呢?盧梭認為還有另一種獲得優越感的方法,那就是故意壓制那些在你下面的人,阻止別人往上爬,你的位置就不會被別人取代。盧梭認為,人類社會的許多痛苦都源於這種心態。如果下屬表現得比上司好,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往上爬,有一天可能會超過上司,因此,上司必須壓制下屬,以保持自己的優越感。
所以,盧梭說:“對名譽的渴望使所有人都成為競爭對手。”這是盧梭批判不平等的關鍵,要判斷一個國家的質量,你可以看看社會不平等對其人民福祉的破壞程度。
amour-propre 的積極作用
到目前為止,amour-propre 似乎只有負面後果,但盧梭實際上認為,比較的心態也可以帶來好的結果。因為渴望競爭榮譽,成為最好的人,也帶來了人類文明的許多發明和創造。
比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都尋求流芳百世,或者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各國運動員都渴望出類拔萃,這種心態讓他們能夠突破人類潛能,達到新的高度。如果你讀名人傳記,你會發現許多偉人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其潛在動機就是為了讓別人驚嘆,證明自己是最有天賦的。
在這些例子中,我們看到 amour-propre 可以帶來積極的好處,激勵人們做對文明社會有益的事情。所以盧梭的理論非常辯證,他並不是說對優越感的渴望都是壞的,而是說同樣的人類欲望創造了文明的許多邪惡,但也創造了許多傑作。
不平等持續存在的原因
盧梭首先揭示了不平等的起源不是自然人性,而是被腐蝕的 amour-propre 人性,然後他批判了不平等帶來的各種邪惡。最後,盧梭想進一步問,為什麼不平等會導致這麼多社會問題,為什麼每次不平等出現在一個社會中,它都會像瘟疫一樣蔓延,不平等可以在所有人類社會中看到。如果不平等帶來這麼多邪惡,社會上的人難道不應該盡力避免它嗎?
盧梭的回答也令人驚訝,他認為,因為那些被不平等壓迫的人實際上是積極參與其中的,這個制度只有在被壓迫者的默許下才能繼續下去。首先,既得利益者會向公眾灌輸錯誤的觀念,告訴公眾不平等是自然的,每個人天生就有不同的才能,資本家更富有是因為他們有更多的創業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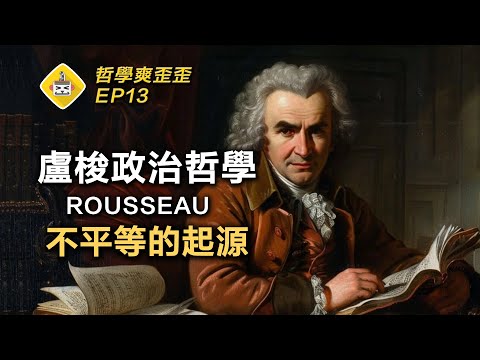
 {#
{#  {#
{#